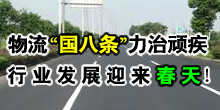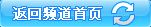20年后的又一个“莱茵兰”
艾登`麦克米伦及其亲信,以及法国总理居伊`莫莱和同僚们面对危机,深深地陷入了历史的沉思。在他们看来,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再世,甚至是一个新出现的希特勒。在1958年的夏季和初秋,艾登仿佛看到,纳赛尔正在推行一套似曾相识的扩张计划。在他看来,纳赛尔所著的《革命哲学》读来颇似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纳赛尔也希望创建一个帝国。他在书中强调,阿拉伯世界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控制石油——“文明的命脉”——与使用暴力相结合。纳赛尔宣称,失去了石油,工业国的所有机器都“不过是一堆锈迹斑斑、无法运转和毫无声息的废铜烂铁而已”。艾登已经作过妥协的尝试。他曾经运用巨大的个人威望在1954年同埃及解决了英国军队撤离运河区的问题,并且因此受到保守党内部一部分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感到,他已经被纳赛尔出卖了。纳赛尔同希特勒一样,他们所签署的文件并非就是他们的诺言。违反国际协议和占领运河的行动难道不是又一个莱茵兰吗?进一步地试图迁就和绥靖纳赛尔难道不是又一个慕尼黑吗?艾登不想再重温这一切了。如果必须对纳赛尔动用武力,那么最好马上动手,切莫拖延。
莫莱总理对设在布痕瓦尔德的德国集中营记忆犹新,并且与艾登所见略同。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亨利`斯帕克也是如此。他在危机期间写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我不想对您隐瞒,我的脑海中索绕着对希特勒时代初期所犯错误的记忆。这些错误使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华盛顿并不像欧洲那样迫不急待。不过,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就如何对付纳赛尔达成一致意见,但归后还是制订了一项以防成万一的计划,以便应付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一决雌雄可能导致的石油危机。艾森豪威尔批准成立一个“中东应急委员会”,以便制定在运河关闭情况下的西方石油供应方案。该委员会与“英国石油供应咨询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通讯联系。
9月份,艾森豪威尔在致艾登的信中坚持认为“使纳赛尔身价倍增”是危险的举动。对此外交部常务副大臣伊马`柯克帕特里克给予了尖刻的答复:“我希望总统是正确的,但是我确信他错了……如果我们退缩,而纳赛尔巩固了他的地位并且逐步接制了产油国,那么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就能够并且下决心毁掉我们。如里我们有一年或者两年得不到中东石油。我们的黄金储备就会荡然无存。如果我们的黄金储备荡然无存,英镑区就会解体。如果英镑区解体,而且我们没有储备,那么我们就无力在德国和任何其他地方维持驻军。我怀疑,我们是否将有能力支付最低限度的必要的防卫开支。而无力防卫的国家是毫无希望的国家。”
就在同一个月,苏伊士运河危机仍在孕育之中。颇受艾森豪威尔赏识的得克萨斯石油富翁罗伯特`安德森,以总统私人智囊的身份秘密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他的目的是要沙特阿拉伯人对纳赛尔施加压力。在利雅得,安德森警告沙特国王和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说,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将开发出远比石油更廉价和更高效的能源,从而可能使沙特和所有中东的石油变得一钱不值。如果运河被当做一种敲诈勒索的工具,那么美国就不得不把这种技术提供给欧洲人。
这种替代能源是什么呢?沙特国王问道。
安德森回答说:“原子能。”
无论是沙特国王还是读过一些关于核电站书籍的费萨尔亲王似乎都没有被打动,也没有对沙特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表示半点怀疑。他们对安德森的警告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的关键决策人物对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的前景已经疑窦丛生。他的结论是,只有动武才能对纳赛尔发生效力。
动武
1956年10月24日,包括双方外交部长在内的英国和法国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在巴黎郊外色佛尔的一间别野里,秘密会晤了包括戴维`本古里安、摩西`达扬和西蒙`佩雷斯在内的以色列最高级代表团。三国达成了一项谅解:以色列为了对付埃及的威胁和军事压力,将穿越几乎荒无人烟的西奈半岛,对苏伊士运河发动军事攻击。英国和法国将就保护运河发出一项最后通碟。如果战斗继续进行——这将是确定无疑的——他们将进入运河区,以保护国际水道。英国和法国的最终目的将是实现运河问题的解决,并且在可能情况下,在此过程中推翻纳赛尔。
就在缔结色佛尔秘密条约的前一天,埃及和叙利亚成立了在埃及控制下的联合军事指挥部。翌日,约旦也加人了联合军事指挥部。一切已成定局。
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政治事件和个人风波,使苏伊士运河危机更加复杂。10月24日,也就是色佛尔会议的同一天,苏联红军部队开进了布达佩斯,去镇压匈牙利爆发的反对苏联控制的革命。然后,安东厄`艾登的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1956年6月,艾森豪威尔因患肠炎而不得不动了手术。因此,就在冲突迫在眉睫的关口,大西洋两岸的两位主角都已健康状况不佳。
经过几个月的踌躇和拖延之后,事情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10月29日,以色列攻入西奈,开始履行色佛尔协定。10月30日,伦敦和巴黎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宣布了占领运河区的意图。同一天,苏联军队从布达佩斯撤出,并且做出了不干预的许诺。翌日,10月31日,英国轰炸了埃及的机场,埃及军队开始匆忙从西奈半岛撤离。
苏伊士运河行动使美国大吃一惊。艾森豪威尔在南方的竞选旅行期间第一次听到了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消息。他怒不可遏。艾登出卖了他。他们在无意之中很可能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国际危机,包括与苏联的直接冲突。而且,行动的时间距美国举国关注的总统大选只差一周。艾森豪威尔在盛怒之下,打电话给唐宁街10号,并且在电话中大发脾气。至少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当时是这样做的。其实,他当时正处于癫狂状态,甚至没有弄清接电话的是艾登的助手。没等对方问清他的姓名,这位总统就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倒霉的助手臭骂了一顿。对方的电话尚未来得及传给艾登本人,他就把电话挂断了。
11月3日,轮到杜勒斯被送进医院了。他被确诊为患有严重的胃癌。他的胃被切除了一大块。到此为止,关键人物之中已有三位病魔缠身,从杜勒斯停止工作开始,美国的日常外交政策管理便易手于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此人曾经组建伊朗财团,被英国人认为是一个厌恶英国的人。
由于后勤供应、计划不同以及艾登的犹柔寡断等原因,英国和法国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的数日之内,并没有立即行动和入侵运河区。在此期间。纳赛尔制造了一场最严重的大破坏。他凿沉了几十艘填满石块、水泥和旧啤酒瓶的船只,有效地阻塞了水道。从而封锁了石油供应。而保证石油供应安全正是英法进攻的直接理由。叙利亚按纳赛尔的指示,破坏了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沿线的泵站,进一步减少了供应。
英国人在策划如何在纳赛尔关闭运河情况下避免石油短缺的那几个月之中一向以为,美国会用其石油供应填补所有的缺额。事实证明,这种设想是大错特错了。英国既打错了算盘,也没有考虑到美国总统大选的日期。艾森豪威尔拒绝实施任何应急供应方案。他对助手们说:“本人认为,挑起这次行动的人应当自己去解决他们的石油问题,自己去下油锅。”石油成了华盛顿对其西方盟友加以惩罚和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艾森豪威尔不但没有向美国的盟友供应石油,反而实行了制裁。
11月5日,以色列已经巩固了对西奈和加沙地带的控制,并且稳稳地控制了蒂朗海峡。同一天,英国和法国军队开始对运河实行伞兵攻击。在此前一天,苏联军队已经重返布达佩斯,并着手镇压匈牙利的暴动。苏伊土事件的同时发生,妨碍了西方对匈牙利起义和苏联干预采取任何有效的共同对策。莫斯科反而指责英国。法国和以色列是“侵略者”。苏联还以军事干预相威胁,甚至威胁要对巴黎和伦敦实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明确指出,任何这样的攻击都将导致对苏联的毁灭性反击。
磨难
尽管艾林豪威尔作出了答复,美国政府对英国和法国的怒气依然未消。从华盛顿传出的信息依然未变:它们同意诉诸军事行动,英国和法国必须住手。11月6日,艾森豪尔以压倒多数大胜阿德莱`史蒂文森。同一天,英法同意就地停火。它们到这时为止,只不过在运河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而已。对他们来说,开战还不到一天,自由使用运河这个战争目标就已经化为了泡影。华盛顿明确表示,仅仅停火是不够的。它们必须撤军。以色列也必须这样做,否则它将受到华盛顿的经济报复。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私人顾问说,绝不可“惹得阿拉伯人对我们恼火”,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发动一场全中东规模的石油禁运。
没有美国的援助,西欧所有国家很快就会出现石油短缺。冬季正在临近,石油储备仅够数周之用。由于运河断航和中东输油管无法使用,西欧3/4石油的正常运输渠道已被切断。除此之外,沙特阿拉伯对英国和法国实行了禁运。在科威特,一系列破坏行动使该国的供油系统停止运行。当美国考虑对英国和法国实行石油制裁的风声吹到英国内阁埃及委员会的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把双手举向空中说到:“石油制裁!那就全完了。”11月7日,英国政府宣布,将石油消费量减少10%,当艾登步入议会下院的时候,工党反对派嘘声大作。持批评态度的议员们宣称,如果要发放定量卡的话,那么定量卡上应当印上安东尼`艾登的头像。
11月9日,艾森豪威尔出席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开始考虑帮欧洲人一把。他提议石油公司应根据一项重大供应计划实行合作。他笑着说,“尽管安东尼`艾登顽固不化”,他仍将批准石油公司根据国家安全利益运作,并且使它们不会因此而受到反托拉斯法的制约,但是,万一石油公司的首脑人物因参与这样一个计划而被投入监狱,又当如何呢?总统放声大笑地说,那他就撤免他们。俣是他也明确强调,这一切只不过是一项应急方案。在英国和法国实际开始从埃及撤出之前,任何应急石油供应计划都绝对不会付诸实施。欧洲人悲伤地抱怨说,美国人要让英国和法国继续经受磨难,以此对它们加以惩罚。国际石油公司眼看着石油短缺日甚一日,便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但是正如一位石油公司的董事所言:“政府一口回绝。”
从另一方面来说,英国经济也是脆弱的。它的国际金融业很不稳固。对苏伊士运河的军事攻击刚一开始,就开始发生英镑挤兑。英国坚信,挤兑是在默许之下进行的,可能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支持和挑唆。在美国的唆使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了伦敦提出的紧急金融援助请求。英国驻华盛顿使馆的经济公使向伦敦报告说,他在寻求急需的金融援助时,在华盛顿到处碰壁。
11月中旬,联会国“维持和平”部队开始到达埃及。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指出,磨难并没有结束。在英国和法国部队撤出埃及之前,不会成立中东应急委员会。一场石油荒巳迫在眉睫。艾森豪戚尔在写给当时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的英国将军洛德`伊斯梅的信中道出了对“自由世界卷入的悲哀”。他“对于西欧的燃料和金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重申,他不希望“与阿拉伯世界交战”。他说,以上最后一种考虑是“无法公开谈论的极其微妙的事情”。伊斯梅复信表示对来信的赞赏,但暗地里却警告艾森豪威尔,下一年春季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可能因缺油而实际陷于瘫痪之中。11月末,英国和法国终于保证迅速从苏伊士运河撤出它们的军队。这时,艾森豪威尔才批准成立了中东应急委员会。美国人赢了。他们使英国和法国在纳赛尔那里遭到失败和屈辱之后,又遭到了新的失败和屈辱在这一混战之中,只有纳赛尔才是唯一的胜利者。
克服危机
12月初,在运河关闭一个月之后,由于英国和法国受挫和整个酉欧处于能源危机的边缘,应急供应计划终于付诸实施。这种所谓的“石油救援”是欧洲和美国的政府与石油公司的合作行动。
在大部分情况下,中东的石油生产并没有中断。问题首先出在运输方面。解决办法就是从其他供应来源取得石油。由于运输距离较近和行船时间较短,同样的一艘油轮从西半球向欧洲运输的石油可以比从波斯湾经好望角向欧洲运输的石油多一倍。因此应急委员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油轮的大规模重新调度,以便使西半球像20世纪40年代末那样再次成为主要供应来源。调整油轮的航线、石油公司联合使用油轮、实行易货供应,一切措施都要为以最快速度和最有效方式运送石油服务。
欧洲国家为了确保被称做“糖罐”的应急供应石油能够在各国之间公正地分配,也进行了广泛的努力。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成立了一个石油使用情况、储备水平和当地能源供应状况基础上制订的方案,实行石油分配。定量供应和其他需求限制是石油求援的补充措施比利时禁止私人在星期天驾车。法国把石油公司销售量限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前的70%。英国增设了新的石油税,因而导致汽油柴油价格上涨和伦敦出租汽车费的上涨,为后人留下了“苏伊士六便士”的笑谈。发电厂则受到鼓励实行以煤代油。到12月底,英国已经实行了汽油定量供应。
尽管首要在于调度油轮,但石油供应量本身也并不充足。据估计,西半球必须显著增产,才能满足西欧的需要,额外石油供应将大量来自于拥有很大剩余生产能力的美国。国际石油公司如饥似渴地在美国原油市场上搜寻能够用于石油救援的一切额外供应。然而,无论是石油公司还是有关国家的政府都忽视了得萨斯铁路委员会。后者在1957年冬季的关键性的几个月中,丝毫不允许增加运量,并且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剩余能力,令所有其他石油公司惊恐不安。这是独立石油生产商与大型石油公司之间由来已久的斗争中的一场新较量。新泽西石油公司董事会的一份内部备忘敏锐地指出,铁路委员会代表了那些“通常只有国内利益”的得克萨斯独立生产商的观点。它担心,如果国内的原油和汽油存货增加,而欧洲却不增加定货,石油价格就会下跌。不管怎样,它所希望的是提高价格,而不是降低价格。
该委员拒绝大幅度增产,招来了一场反对的轩然大波。英国石油公司的埃里克`德雷克说,这“对欧洲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新泽西石油公司的一位驻欧洲代表说,这是“灾难性的”,并且会使该公司对欧洲的供应量减少50%。艾登和麦克米伦都亲自对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的政策表示了抗议。英国报界指责这家隐藏在得克萨斯深处的名不见经传的神秘机构。针对英国的抱怨,年迈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委员汤普逊上校反驳说:“我们已经给它装运了不少原油,而它却批评我们没有按它的命令运出所有的原油。美国显然依然把我们看做是一个省或者是一块自治领。”
到1958年春季为止,主要由于石油救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成效,石油危机终于接近尾声。将近90%的供应缺额已经得到弥补。在欧洲,及时采取的储备措施加上温暖的气候,使剩下的缺额也大部分得到了弥补,因此实际短缺额是很小的。从总体上看,当时的欧洲经济还不像后来那样易受石油供应中断的伤害。1956年,石油只占全部能源消费量的20%。欧洲经济虽然正处于轻变之中,但仍然主要是一种煤炭经济。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了变化。
1957年3月,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部分开通了。4月份。苏伊士运河经过清理,已经可以通过油轮。纳赛尔赢得了胜利。苏伊士运河已经无可争辩地归埃及所有,并且由埃及经营。虽然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导航员的衣着井不像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前任那样干净利落,但他们却相当胜任导航工作。波斯湾产油国渴望恢复石油供应。科威特因缺乏运输能力,石油产量已经下降了一半。4月份,美国政府中止了应急石油救援计划。5月中旬,英国政府停止了石油定量供应,然后采取了最后一道不情愿的措施,即指示“英国航运部门使用苏伊士运河”。以此为标志,苏伊士运河危机才真正地落下了帷幕。
“艾登爵士”退场
一位美国的参与者在回忆那场危机时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那几个月非同寻常,上演了精彩的喜剧,卑劣的阴谋剧和深刻的悲剧。但是从个人和民族的角度来看,主要还是悲剧。”对于被纳赛尔称做“艾登爵士”的安东尼`艾登首相来说,那是一幕巨大的个人悲剧。在那之前,他一向靠料事如神、富于勇气和外交技巧而政绩辉煌。然而,当纳赛尔凿沉船只的时候,艾登的声誉也被一同沉入了运河的水底。艾登的医生告诉他,他的健康状况已不适宜担任首相工作了。1957年1月,他辞职了。
最先得知此信的人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当艾登约他到唐宁街10号小客厅会面的时候,他就住在隔壁的唐宁街11号。麦克米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那个凄凉的冬季下午,我可以看出,他依然是那样富有朝气,那样活泼愉快,那样温文尔雅。这是1914~1918年战争期间青年军人的典型特征。那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的幸存者们往往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就像一批不完成任务誓不罢休的战士。他和我就是怀着这样的精神步入政坛的。现在,他经过长年奋斗,已经攀上了权势的巅峰,但是却被一种神秘的然而又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击倒了。”怅然若失的麦克米伦心情凄楚地沿着通道走回到唐宁街11号财政大阻的官邸。第二天早晨,他正在官邸中坐在一幅格拉斯够通的肖像画下读着《傲慢与偏见》以调理心绪,突然接到了请他去王宫就任首相的电话。
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国的一个转折点。它造成了英国的文化、政治和国际地位的严重断裂。苏伊士运河并不是英国衰落的先兆,而是使早就开始的衰落从此大白于天下。英国不再是第一流强国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以及国内的分裂不仅严重消耗了它的财力,而且也严重削弱了它的信心和政治意志。艾登坚信,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没有做错什么事。数年之后,伦敦《泰晤士报》对安东尼`艾登做出了如下的评论:“他是相信英国是伟大强国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亲眼看到英国被危机证明不是伟大强国的首相。”此语堪做大英帝国的墓志铭,也道出了艾登的心境。
未来的安全:油管与油轮
苏伊士运河危机给国际石油工业带来了不少启迪。尽管运河已经恢复运营,石油公司对它的可靠性却已失去了信任。接着,石油公司和西方国家政府就扩建输油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但是,叙利亚禁止使用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一事表明,切断输油管也是易如反掌。显然,输油管并不是解决石油安全过境问题的唯一对策,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在围绕苏伊士运河生命线的一切激烈争论之中,有一个方案被人们忽视。如果说运河和中东输油管都易受损害,那么还有一个更安全的替代方案,即使用环绕好望角的航道。为了经济和实用起见,倘若利用这条航道向西欧供应石油,则必须使用装载能力更大、船体更大的油轮。然而工业界一般认为,从物理学角度而论,这种油是无法建造的。可是,日本的造船厂发挥了柴油发动机和优质钢材的优势,根快就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壳牌石油公司高级经理约翰`劳登回忆说:“1956年,油轮的船主们还在说,大船过于昂贵,其燃料费用也太高了。令我吃惊的是,日本人不久就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建造这种油轮了。”事实证明,这种油轮不仅出奇地经济,而且也符合安全标准。因此,超级油轮也同英国声势的衰落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崛起一样,成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产物之一。
破镜重圆
苏伊士运河危机过后,英国人和法国人仍然对美国人怀恨在心。英国驻美国大使在1957年初措词尖刻地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像美国童子军一样看待殖民主义、联合国和玩弄辞令策略的有效性……他的天性和挽救健康的需要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无所做为的总统之一。”
在危机期间,美国竭力试图利用阿拉伯产油国来巩固它的地位。艾森豪威尔本人非常强调“把沙特国王扶植成中东地区的重要人物”,以便取代纳赛尔。他还向阿拉伯产油国明确表示,美国愿意为“在西欧恢复中东石油的市场”而努力。除了这种考虑之外,也有可能进一步支持中东的稳定的亲西方政府,把它们作为遏制苏联扩张主义的堡垒。英国和法国无疑同意这两项战略目标。它们之间的分歧在于手段,而不在于目的。
大西洋两岸都承认,有必要弥合苏伊士运河危机造成的分裂。以“处变不惊”而出名的新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后来承认他的内心经常因紧张恐惧而痛苦万状。他与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携手共事,并且保持着友情和相互尊重。当人们提到麦克米伦可能接替艾登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形容他是一位“坦诚、细致的人”,麦克米伦还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在接受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沉痛教训之后,他说,“我们的一切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华盛顿的统治者手中。”这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对于艾森豪威尔的美好祝愿,麦克米伦答复说:“我对于将使我头痛的问题并无幻想。但是,33年的议会生涯使我锻炼得坚韧不拔。我希望,这并不会减少我的幽默感。”
中东和石油以及欧美联盟的裂痕当然是一些最令他头痛的问题。正式的和解进程开始于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参加的百慕大会议。会议是1957年3月在大洋高尔夫河俱乐部召开的。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麦克米伦着重考虑了石油问题。他调来了一张标明各石油公司在中东的位置的地图和一份石油公司的“大系表”。石油与中东安全两个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诚如艾森豪威尔后来所说,就石油问题进行了“非常坦诚的谈话”,其中包括探讨鼓动建造超级油轮的可能性。苏伊士运河使所有西方强国都领教了变化多端的中东局势。在百慕大,英国强调,保持科威特和海湾沿岸其他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国家的君主都极易受到纳赛尔式政变的损害。双方同意,英国需要尽一切可能确保海湾的安全。麦克米伦把中东石油称为“世界的头奖”,敦促两国政府进行合作,以实现该地区的长期和平与繁荣。他说,这就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曾经使用过的那种“共同方式”。百慕大会议的确弥合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分裂。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许诺,每周以个人名义“无拘束地”互致一次信件。总而言之,这两个国家在中东确有共同的目标。但是,苏伊士运河危机已经富于戏剧性地证明,在未来的岁月中,执牛耳者将是美国,而不再是英国了。
1970年,在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14年以后,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的胜利,爱德华`希思接任首相。他在唐宁街10号为当时已是埃文伯爵的安东尼`艾登举办了一次晚宴。保守党党魁希思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也有同样的头衔艾登以贵客身份重返唐宁街10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心境美好的夜晚。希思发表了诙谐和优美的讲话之后,艾登起身,即席致答。他为英国人民进行了特别的祈祷,祈祷他们在北海水下发现一个“石油湖”。这恰恰就是英国人在1970年开始做的事情,尽管他们未能及时利用这一发现,以避免爱德华`希思在另一次能源危机中垮台。如果英国人知道或者猜测到这样一个石油湖的存在,1956年就会是另一番光景了。(来源:中信出版社)
页次:2/2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尾页 Go: |